(完)为裴延诞下麟儿后 我觉得此生已圆满 却无意听到他和管家对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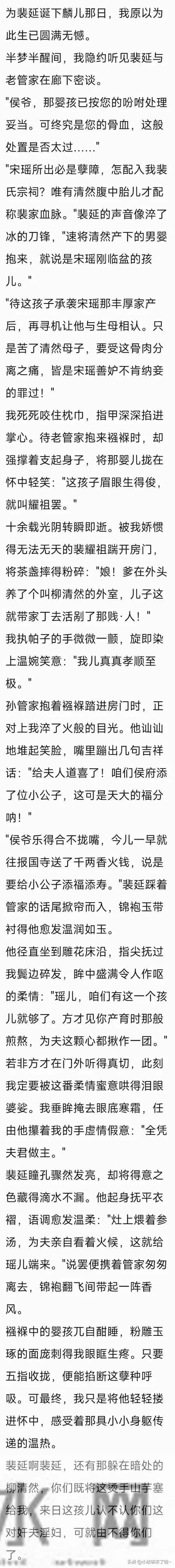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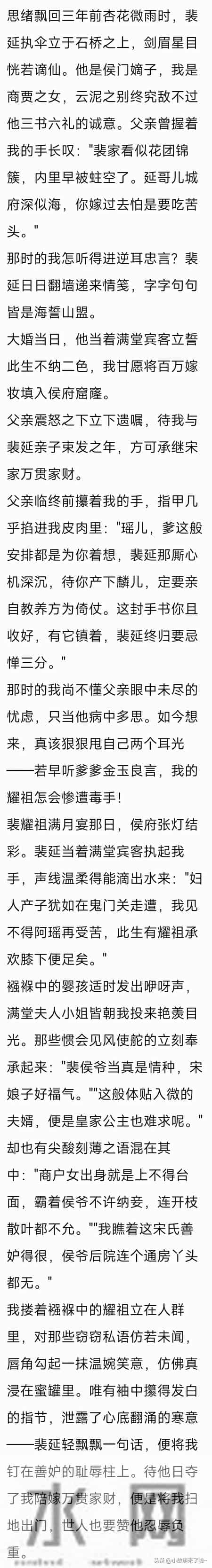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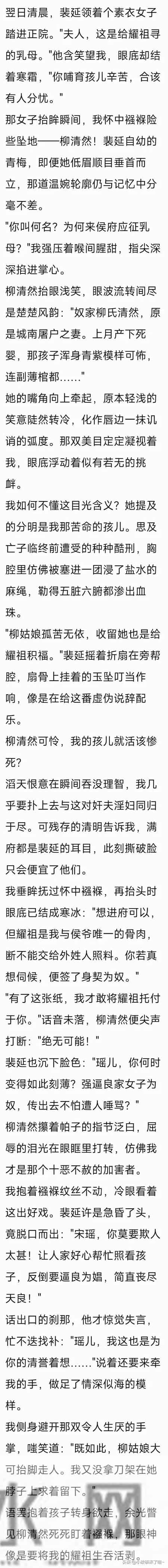
一个时辰后,柳清然签了卖身契,搬到我院子的西厢房。
裴延迫不及待地抱着孩子往西厢房送,美其名曰让我休养。依然是平时虚假模样。
我站在西厢房窗边,透过缝隙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团聚的画面。
柳清然倚在裴延臂弯里,怀里搂着襁褓中的裴耀祖,哭得梨花带雨:"裴郎,为了你和孩儿,我连清白身子都舍了,你往后可不能薄待我。"
裴延垂首吻去她眼尾泪珠,嗓音温柔得能掐出水:"清然,我裴延对天起誓,此生必不负你。瞧你受这等委屈,我五脏六腑都揪着疼。你再忍些时日,待咱们耀祖承袭爵位那日,我即刻休了宋瑶那毒妇。"
他指尖抚过柳清然鬓边碎发,眼底闪过狠厉:"到时定要让宋瑶跪着给你端洗脚水,方能解你心头之恨。"
柳清然破涕为笑,将脸颊贴着婴孩襁褓轻蹭:"我别无所求,只愿常伴裴郎左右。"
裴延朗声大笑,将母子二人圈进怀中:"如今咱们才算得上天伦之乐。耀祖有你这般慈母教养,日后必只认你一个娘亲。待这孩子执掌侯府基业,宋家百年家业尽数归咱们所有。"
他执起柳清然柔荑,目光灼灼:"你虽顶着奴婢名分,我必让你享尽荣华。明日起便让厨房备下燕窝粥、鱼翅羹,你且先用参汤漱口,鲍鱼切脍开胃。"
柳清然娇嗔着捶他胸口,屋内顿时漾开两人肆意的笑声。
我端坐黄花梨木椅中,冷眼看着雕花窗外晃动的剪影。且由着他们笑罢,这好日子……怕是要到头了。
翌日清晨,我正用着银耳莲子羹,裴延便携着柳清然闯进院来。晨光里那对男女并肩而立,倒真像画里走出的璧人。
我执勺的手未停,舀起一汪晶莹送入檀口。裴延却大步上前,劈手夺过青瓷碗盏,瓷器与桌面相撞发出脆响。
"宋瑶!你竟还有心思用膳?"他额角青筋跳动,怒目圆睁,"侯府后宅让你管得乌烟瘴气!今日若非我亲自去瞧耀祖,还不知你这毒妇如此苛待清然!"
侍女翠云按捺不住要上前分辩,我轻抬皓腕将人拦住。抬眸看向暴怒的夫君,以及他身后那道得意目光。
"夫君这话从何说起?"我取出帕子拭了拭唇角,"我何曾苛待过柳氏?她一个签了身契的奴婢,也配劳动本夫人亲自过问?"
裴延闻言怒火更盛,重重拍案:"宋瑶!你竟如此刻薄!清然哺育耀祖劳苦功高,你非但不知感恩,反倒用些鸡汤残羹敷衍,那些燕窝鱼翅是一点看不见。"
“难为清然刚刚还帮你解释,说你操持府里的事务太操劳了,是下面人做错了,跟你无关,但是我看你这么悠闲地吃着早膳,哪有太操劳的样子?
“你就是舍不得那些燕窝鱼翅野山参,舍不得对耀祖好。”
一顶顶沉甸甸的罪名劈头盖脸砸来。
倚在雕花木椅旁的柳清然纤纤玉指拽住裴延的锦袍袖口:"侯爷且息怒,夫人定是忙昏了头才疏忽的。"她执起素帕拭泪,"都怪妾身出身卑微,合该用些粗茶淡饭。"说这话时,那双含情目却带着三分讥诮朝我瞥来,全然不顾满屋子侍立的仆妇。
裴延神色缓和,轻抚她手背,转脸对我冷笑:"看来夫人这管家主母当得力不从心,倒不如寻个得力助手……"
我垂眸抚着翡翠镯子,心头雪亮。这对男女天不亮就发难,原是惦记着中馈大权。
"侯爷错怪妾身了。"我抬眼浅笑,"给清然姑娘备的物件,皆是比照着皇室皇子公主的乳母规制置办的。"
这番镇定自若倒让两人怔忡。柳清然率先回神,贝齿轻咬朱唇:"夫人莫要诓骗妾身,妾身虽是市井小民,却也知晓皇家岂会用清粥小菜打发人?夫人这般信口开河,若传到宫里……"
"宋瑶!"裴延猛然拍案,青瓷茶盏震得叮当响,"你如今怎变得如此癫狂?不过数落两句便胡言乱语,莫不是产后得了失心疯?"
他声如洪钟,全然不顾我正房夫人的体面。
贴身丫鬟翠云急得跺脚:"侯爷明鉴,夫人早吩咐小厨房备了催乳的膳食,都是太医开的方子!"
裴延眉峰紧锁,显是对下人忤逆颇为不悦。我上前半步将翠云挡在身后:"今晨特请了太医院陈太医,依着医案拟了通乳的汤剂,这会子该熬好了,侯爷可要验看?"
话音未落,陈太医已掀帘而入,身后捧着红木托盘的婢女热气氤氲。
"老朽给夫人请安。"白须老者指着青花瓷盅笑道,"这野山参炖猪蹄最是滋补下奶,老朽亲自盯着火候……"
裴延脸色微变,陈太医是御前红人,寻常公侯想请都请不来。我能劳驾他,全仗着父亲当年救过太医署一场大火。
我转身对柳清然颔首:"清然姑娘请用,这可是本夫人命人守着砂锅炖了整宿的。"
陈太医在旁帮腔道:"可不是嘛,这等成色的野山参金贵得很,便是宫里小主子的乳母都未必享用这个待遇。"
裴延被这番话噎得哑口无言,显然没料到我会提前备下这手。柳清然贝齿紧咬朱唇,纵使心头千般不愿,也只能颤巍巍伸出素手捧起海碗。
她垂眸望着碗中漂浮油花的猪蹄汤,两道细眉拧成麻花状,水汪汪的眸子楚楚可怜地望向裴延。奈何有外人在场,裴延只能佯作未见,袖中双拳却已攥得指节发白。
我暗自冷笑,提高声调道:"侯爷可听真了,这支百年野山参价值百两雪花银,我整根都炖进汤里。为着耀祖能茁壮成长,我可是掏心掏肺,若有哪个不长眼的打翻汤碗害我儿营养不济……"说到此处,我刻意顿住,目光如刀扫过柳清然惨白的脸,"便休怪我翻脸无情,当场家法处置!"
"夫人说笑了。"陈太医极有眼色地接话,"谁敢编排夫人心肠狠辣?老朽行医半生,见过多少高门大户,论对乳母的体恤,夫人称第二便无人敢称第一。若有那不长眼的嚼舌根,老朽头一个不答应!"
裴延被这话堵得面皮发紫,喉头滚动半晌终是未发一言。柳清然见状,只得含泪捧起汤碗,刚抿了一口便扭头干呕。
"怎的连盐都不放?"她泪眼婆娑地控诉,"奴婢知晓夫人看不上妾身,可这般作践人……"
"放肆!"陈太医猛地一拍案几,"乳母忌口荤腥调料是常理,莫说公侯府邸,便是贩夫走卒家都懂的规矩!贵府怎的寻来这般不懂事的乳母?莫不是被牙婆蒙骗了?"
裴延颜面顿时挂不住,忙不迭作揖赔罪:"太医息怒,定是下人不懂规矩,本侯定当严惩!"
"还不快喝!"裴延转身对柳清然厉声呵斥,后者委委屈屈捧起汤碗,每咽一口都像吞刀片般痛苦,俏脸扭曲得活像打翻的颜料铺子。
我端坐太师椅上看得痛快——特意交代厨娘撇去漂油,文火熬得浓稠如浆。此刻汤汁未加半粒盐,腻得能粘住筷子,正合我意。她既要装贤良母亲,我便成全她这番"慈母心肠"。
柳清然边呕边灌,两碗汤水耗了足足一个时辰。待她踉跄抱起裴耀祖夺门而出时,整张脸已白得透光。陈太医不屑地嗤笑:"这般娇滴滴的模样,不知是来做乳母还是当主子的。"
送走陈太医后,裴延铁青着脸质问:"你何苦与清然过不去?人家卖身为奴已够可怜,又尽心照料耀祖,你竟容不下她?"
我执起茶盏轻啜一口,慢悠悠道:"侯爷这话奇了,我何曾刁难于她?不过是按规矩办事罢了。倒是侯爷,往日总夸我贤良淑德,如今倒像是瞎了眼。"
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裴延:"侯爷何以认定我容不下她?可是她做了什么亏心之事?"
裴延呼吸一窒,猛地别过脸去:"宋瑶,我原以为你与那些俗世女子不同,温婉贤淑得如同空谷幽兰,如今看来竟也是个善妒的深宅妇人,当真是我看走了眼!"
语罢他甩袖便走,玄色衣摆划出凌厉的弧度。
我轻启朱唇,语气淡漠如霜:"往后柳姨娘的膳食皆按陈院判的方子准备,还望侯爷莫要横加干涉。陈院判最忌旁人质疑他的医术,若是在圣上跟前说漏了嘴……"
裴延猝然停住脚步,背影明显僵了僵,最终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:"随你的便!"
待那道颀长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,我朝侍女翠云使了个眼色。主仆二人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,果见裴延径直往西厢房方向去,想来是安抚他那心尖宠去了。
窗棂下,柳清然抽噎得如雨打梨花,裴延正将她圈在怀中柔声劝慰。
"裴郎,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……"
"然儿放心,这口恶气我定会替你讨回来。"裴延眼底闪过阴鸷,"只是需从长计议,再容他们嚣张几日。"
他抚着柳清然的后背,声音陡然转冷:"从今往后,我再不踏足宋瑶的院子,就让她独守空房好好反省!待她熬不住来求我时,我便让她跪在祠堂给你赔罪。"
我倚着廊柱轻笑出声,这男人莫不是得了臆症?且不说侯府中馈仍在我手中,单是祖父留下的暗桩就够他喝一壶的。
柳清然抽抽噎噎地抬眸:"那……那苦药汤子还要继续喝?"
"良药苦口。"裴延耐心哄劝,"陈院判特意交代过,奶娘都是这般进补的。你若想亲自哺育耀祖,这些苦头便少不得要受。"
说着从袖中掏出张银票:"过两日我让宋瑶再寻两个奶娘来,届时你只管使唤她们便是。"
柳清然这才破涕为笑,两人耳鬓厮磨间,呼吸渐渐急促起来。
"小姐!"回程路上翠云气得直跺脚,"这等腌臜货色,咱们何不直接求了和离书,省得在此处受窝囊气!"
我望着天际流云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玉佩:"和离?那岂非太便宜他们了?我要让这对奸夫淫妇尝尽求而不得的滋味,方能告慰我儿在天之灵。"
"您且瞧着吧。"我抚过鬓边珠花,眼底寒芒乍现,"既然侯爷要添两个奶娘,我定当好好物色,挑两个最'贴心'的送去西厢房。"
此后十日,裴延果真未曾踏入我院中半步,连用膳都借故推脱。
月华初上柳梢时,他总鬼鬼祟祟往柳清然院里钻。我早看穿这男人在等我低头服软,偏不遂他的意。如今倒好,我夜夜安眠,日日好胃口,连贴身丫鬟翠云都打趣我:"姑娘这几日皮肤都透着光亮呢。"
反观那对野鸳鸯,倒是一个赛一个憔悴。养孩子哪是嘴上说说这般容易?小祖宗半夜嚎哭,隔两个时辰就要喂一次奶,便是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这般折腾。
这不,没等我主动示弱,裴延倒先沉不住气了。正午时分,我正捧着粳米粥小口啜饮,他便大马金刀坐到我对面,下巴微扬着抛出句:"可知错了?"
我装聋作哑,只管往嘴里扒饭。且由着他摆谱,待会儿说出更难听的污糟话,没得败坏我食欲。
"既知清然大度不与你计较,你更该懂事些。"他自顾自夹了块炙羊肉,"清然照料耀祖实在吃力,你速去寻两个得力的奶娘帮衬。我这般安排,已是给你台阶下,往日就是太由着你胡闹,日后可莫要再恃宠生娇。"
又絮叨半晌,才施施然端起饭碗。待那道靛青色身影消失在院门,翠云朝着地上啐了三口:"呸!真当自己是盘菜了!"
我慢条斯理拭着嘴角:"让你寻的人可有着落?"
"姑娘放心!"小丫头眼睛发亮,"奴婢按您吩咐,往醉香楼撒了大把银子,老·鸨子办事最是利索,挑了四个顶标致的。"
我轻笑出声:"那便领进来罢。"
从前被裴延哄骗时,我还信这世上有不偷腥的猫。如今可算明白,妻不如妾,妾不如偷,天底下男人都这德行。柳清然虽是他心尖宠,我就不信他能忍得住不沾荤腥。
暮色四合时,两个穿红着绿的奶娘被领进柳清然院子。翠云回来时,嘴角都快咧到耳根:"姑娘是没见着,侯爷瞧见那两位,眼珠子都快黏人家身上了!柳姨娘当即就变了脸色,红着眼圈要撵人,还是奴婢按您教的,说这是陈太医引荐的,原先在宫里侍奉过皇子公主。侯爷当场就翻了脸,骂柳姨娘不懂规矩!"
我摩挲着茶盏冷笑。这才哪到哪?柳清然产后身子未复原,肚皮松垮得跟老倭瓜似的,哪还有往日风情?她若想笼住裴延的心,就绝不敢让夫君瞧见这般丑态。
所以裴延这些日子定是憋屈得慌。
如今这两位妖娆乳母进了府,他还能端得住?
更别说本夫人寻来的可不是寻常乳母,个个身怀绝技。
早年跟着家父学经商时,可没少听说达官显贵家的腌臜事。
那些败落的勋贵府邸最爱豢养扬州瘦马,连带着调教乳母的法子也一套一套的。
这种专供贵人享用的乳母生得蜂腰肥臀,肌肤胜雪,产乳量更是惊人。
可她们的乳汁压根不是喂孩子的,而是专供那些老爷少爷们饮用的。
都说人乳是气血精华,最是养人,自然叫那些纨绔子弟趋之若鹜。
当然这些个乳母最拿手的可不是产奶,而是伺候男人的手段。
经过专门调教,个个把男人心思摸得透透的,拿捏起来易如反掌。
眼下我就盼着柳清然别太不中用,三两下就被这些个狐媚子收拾了。
西厢房那边闹腾成什么样我懒得理会,只管调养自己的身子,倒是翠云日日盯着动静。
那两个狐媚子进府才三天,柳清然就找借口拦着裴延不许他来瞧裴耀祖。
嘴上说着"男儿当以功名为重,岂能沉溺后宅",实则怕裴延跟那两个乳母勾搭上。
毕竟这天底下啊,只有躺进棺材板的男人才能真老实。
这两个乳母可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,哪是柳清然这种黄脸婆能比的?
果不其然,裴延那厮压根把持不住,任凭柳清然如何阻拦,照样雷打不动每日往西厢房跑两三趟。
还假模假式借着探望儿子的名头,跟那两个乳母眉来眼去,直把柳清然气得脸色发青。
翠云还跟我说,裴延不在时柳清然竟动手打了那两个乳母。
"小姐,您要不要去给那两个狐媚子撑腰?再这样下去,她们怕是要被正房夫人拿捏死了。"
最后翠云忧心忡忡地劝我。
我却慢悠悠呷了口茶,摆手让她莫急:"这些个狐媚子能在风月场里混饭吃,自然有她们的本事。"
果然次日翠云就兴冲冲来报,说裴延瞧见那两个乳母脸上的巴掌印,当场就冲柳清然发了通火,夫妻俩不欢而散。
这结果我早料到了,男人啊,最是喜新厌旧。
不过这样正好,该收网了,就等着那条大鱼自个儿往罗网里钻呢。
又过了五日,柳清然竟抱着裴耀祖主动登门求见。
"夫人,奴婢本不该多嘴,可这男人偷腥的毛病实在难改。"
"新来的两个乳母委实不像话,每次侯爷来看小世子,她们就往侯爷跟前凑。"
"奴婢也是替夫人着急,这才来禀报的,您可要留个心眼呐。"
柳清然边说边偷觑我的脸色。
我心中冷笑,面上却适时露出几分凄苦:"自打生产后,侯爷连我院子都不愿踏进一步,我能有什么法子?"
“既然侯爷中意,我也不好横加阻拦,有耀祖承欢膝下便够了。”
柳清然贝齿紧咬,望向我的眼神裹着轻蔑与厌烦,可为了盘算多时的谋划,仍强压火气劝道:“夫人此言差矣,您是堂堂侯府主母,怎能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媚子踩到头上?”
“横竖我是侯府明媒正娶的夫人,守着耀祖过活便知足了。只盼侯爷体恤则个,别弄出些庶子庶女来脏了侯府门楣,倒叫我们耀祖脸上无光。”我执起茶盏轻啜,余光瞥见柳清然脸色骤变。
她确是未曾料到这层利害——若侯爷真留下几房妾室所出的庶子,裴耀祖的世子之位怕是要平添变数。眼见我这般不争气,她气得胸口剧烈起伏,偏生寻不出半句驳斥之言。
我抬手止住她未出口的规劝:“你且退下吧,好生照料耀祖才是正经。只要侯爷舒心畅意,其他琐事我自不会计较。”
柳清然银牙咬得咯吱作响,终是踩着碎步退了出去。行至门边时,我隐约听得她啐骂声穿透雕花门楣:“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,活该被踩进泥里!”
我阖目假寐,恍若未闻。
柳清然刚踏出门槛,便与急匆匆赶来的翠云撞了个满怀。一包药材从翠云袖中滑落,她慌忙捡起塞回袖口,也顾不得行礼便疾步进屋。
我眼角余光扫过,见柳清然顿住脚步,整个人缩在廊柱阴影里,活像只准备偷油的老鼠。
翠云压低嗓音道:“姑娘,这是陈太医亲手调配的方子,待药煎好后哄侯爷服下,只当是寻常补药。这药性烈得很,男子服下便再无生育可能,却半点不伤身子……”
我配合着蹙起眉头:“还是作罢吧,若侯爷真想纳妾便由着他去。左右不过多分些产业给庶子,总好过因这等阴私事伤了夫妻情分。”
“姑娘三思啊!”翠云急得直跺脚,见我心意已决,只得悻悻揣着药包退下。
我望着柳清然隐入回廊的背影,唇角扬起几不可察的弧度——鱼儿,终究是咬钩了。
一炷香的工夫过去,翠云眉眼含笑地踱步归来,朝我微微颔首。
我闭目深吸一口清气,掌心攥得发疼——成了,此刻只需静候佳音。
次日天色未明,裴延跟前伺候的小厮便跌跌撞撞闯进我院门。
"夫人!大事不妙!侯爷他……他口眼歪斜了!"
我垂眸掩住眼底快意,谋划终是得了逞。
待我踏进书房时,满室狼藉映入眼帘。
柳清然面如金纸杵在墙角,钗环散乱得不成样子,想是吓破了胆。
裴延已被仆从七手八脚抬上软榻,我近前细瞧,但见他口角歪斜,十指蜷曲如鸡爪,早昏死过去。
陈太医背着药箱急匆匆赶来,三指往裴延腕间一搭,提笔刷刷写下方子。
"侯爷确是中风之症,往后口不能言,身不能动,只恐要长卧病榻了。"
"按理说侯爷正值盛年,不该这般凶险。必是服了什么虎狼之药,气血倒冲才致如此。"
"这药需日日服食,或许……或许能有转机。"
太医话音未落,下人们已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
柳清然盯着脚边碎瓷片上褐色的药渍,忽地转头瞪向我,眸子里淬了毒般明晰——她终是回过味来了。
我示意翠云去煎药,又向陈太医福了福身。
老太医临出门前长叹一声:"令尊当年救我性命之恩,今日总算还了。姑娘……好自珍重。"
我鼻尖发酸,对着佝偻背影深深拜下去。为着我这私仇,竟教悬壶济世的老者违背医者仁心,实乃罪过。
裴延生性多疑,我院里送去的吃食他从不沾唇。可柳清然不同,那蠢妇递的汤药,他定是毫无防备地饮尽了。
自然,哪有什么立时三刻要人瘫倒的毒药?不过是些麻沸散混着令人心悸的虎狼药,药效统共三个时辰。
如今裴延瘫在床上,侯府上下尽在我股掌之间。
我早已将他贴身伺候的人换了个干净,着人每三个时辰便灌他一碗药汤。
要叫他尝遍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。
待料理完琐事,翠云附耳禀报:"柳姨娘方才偷偷溜出府了,奴婢已派机灵的小厮跟着。您猜怎么着?那贱·人边走边念叨'留得青山在'、'君子报仇'什么的。"
这柳清然倒是个机灵的,算准了我会灭口,竟抢先一步溜了。
听她那话里话外的意思,分明还存着妄念呢。
"裴耀祖可带走了?"
翠云垂首应道:"回夫人,那孽障独自跑的。"
我执起茶盏轻啜一口,眼底泛起冷笑:"她这是要学姜太公钓鱼呢,做着等裴耀祖承袭家业后再现身认亲的春秋大梦。"
"由着她去,且让她在黄粱美梦里多泡些时日。日久天长,待美梦化作泡影那日,才最是蚀骨灼心。"
"即刻将裴耀祖送去城外别院养着,就说我需侍奉侯爷无暇分身,多派些仆从跟着,按着嫡少爷的规制好生伺候。他学成纨绔还是败家子都随他去,只管盯紧了柳清然。便是她乔装成粗使婆子混进去,也莫要打草惊蛇。"
翠云福身道:"奴婢谨记。"
柳清然不是常把"君子报仇十年不晚"挂嘴边么?那我便遂了她的愿,让她再做十年痴梦。我倒要瞧瞧,待黄粱梦醒时,她那张脸会扭曲成何等模样。
裴耀祖果真流着裴延与柳清然的血,纵使无人教导,也将纨绔做派学了个十成十。
五岁稚龄便对下人非打即骂,八岁年纪就懂得糟蹋丫鬟。我曾数次训诫于他,亦严令别院不许留用年轻婢女。
却不知柳清然早在他两岁时,就隐姓埋名潜入别院,以仆妇身份伴其左右。每当我现身别院,这妇人便如老鼠见猫般藏匿,真当我不知她那些腌臜手段?
七岁那年,这对母子已敢在背地里对我口出恶言。
"宋瑶那毒妇,竟将我困在这别院,端的狠毒!"
"待我及冠执掌万贯家财,定要将这毒妇逐出侯府,令她沿街乞食,跪地求饶!"
柳清然非但不加阻拦,反在旁煽风点火:"我儿说得极是,且再忍耐些时日。待你束发之年,便可一雪前耻,为你爹娘报仇雪恨。"
然裴耀祖对生母亦无半分敬重,当即呵斥:"休要再提你是我娘亲!你这卑贱之躯……"
柳清然却浑不在意,仍赔着笑脸:"我儿说是什么便是什么,为娘别无所求,只盼能将宋瑶那贱·人挫骨扬灰。"
提及要我性命时,这妇人眼中迸发的癫狂,竟似要凝成实质。
我悄然隐于暗处,将这番大逆不道之言尽收耳底,始终未曾现身。
裴耀祖十岁生辰刚过,别院便送来书信一封。
信中言辞恳切,道是欲回府尽孝于双亲膝下。
我冷眼看着那封家书在铜盆里化为灰烬,火舌卷着墨香舔舐指尖。裴耀祖这小畜·生倒是长进不少,纨绔成性却也懂得先发制人,十岁稚龄便敢打着继承爵位的旗号回府夺权,还敢在奏折里大言不惭要替我分忧。
果不其然,信到第三日,裴耀祖便带着人马浩浩荡荡杀回来了。柳清然那贱·人仗着有靠山,竟敢堂而皇之跟在孽种身后,见我目光扫去,竟还扬起下巴笑得刺眼。
"多年未见,夫人别来无恙啊。"她涂着丹蔻的指尖掩住朱唇,眼尾挑起得意的弧度。
我懒得施舍她半个眼神,只盯着裴耀祖。这孽障不过十岁年纪,身量竟已与我比肩,玄色锦袍穿在身上倒像模像样。他轻笑一声,稚嫩嗓音里透着诡异的老成:"柳姨这些年照料孩儿劳苦功高,母亲合该备份厚礼相谢。"
"是啊母亲,冤家宜解不宜结。"他上前半步,将柳清然挡在身后,"往后柳姨便在府中住下,正好与母亲作伴。"
我摩挲着腕间翡翠镯,忽然觉得这孽种眉眼像极了他生父。柳清然见我不语,愈发嚣张起来,莲步轻移至我跟前:"夫人可知风水轮流转?不必三十年,只十年我便杀回来了。"
她染着凤仙花汁的指甲戳在我心口,笑得花枝乱颤:"我知夫人心里窝火,可那又如何?侯爷心尖尖是我,世子爷也敬我如母,夫人最在意的两个男人,早成了我的裙下臣。"
裴耀祖适时补刀:"母亲操劳半生也该歇歇了,待礼部批文下来,儿子便送您去别苑安享晚年。"他整了整衣袖,露出与裴延如出一辙的薄凉眼神,"您放心,您那些嫁妆田产,儿子定会好好打理。"
柳清然笑得愈发猖狂,鎏金护甲划过我鬓边:"认命吧宋瑶,这侯府早该易主了!"
我忽地轻笑出声,目光在母子二人脸上逡巡。说来也怪,这孽种生得竟与柳清然有七分相似,尤其是那双上挑的桃花眼。指尖轻轻叩着紫檀木椅扶手,我淡声道:"裴耀祖,你若此刻将柳氏杖毙,我仍认你这儿子。"
柳清然像是听到天大笑话,扶着腰笑得直不起身:"宋瑶啊宋瑶,你莫不是疯了?便是知道真相又如何?证据呢?"
裴耀祖也皱起眉头,稚嫩面庞浮起不悦:"母亲慎言,这般疯话传出去……"
"我知你是裴延与柳清然偷情所生的野种。"我径直打断他,看那母子二人瞬间煞白的脸色,"我亲生的孩儿,早在出生那日便被你们害死了。"
似乎没料到我知道真相,两人都有些愣住。
不过瞬间,两人都反应过来,柳清然更加兴奋和得意:“宋瑶,你这是狗急跳墙了啊,知道这些又如何,你有什么证据?”
裴耀祖垂眸不语,任由柳清然继续趾高气扬。
"这些年你活得憋屈吧?明知养的是我亲儿,却不得不强忍恶心接受,真是痛快至极!"
"现在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,或许还能赏你口残羹剩饭。"
望着眼前洋洋得意的母子俩,我知晓该送他们下十八层地狱了。
轻叩两声掌心,数道人影应声而入。
裴耀祖与柳清然同时僵住,目光齐刷刷投向不速之客。
为首者正是侯府旧仆孙管家,其后跟着位鬓发斑白的中年妇人,末了是裴延生前的贴身书童。
三人甫一进门便齐刷刷跪伏在我脚边。
见此情形,柳清然面色骤变,裴耀祖虽不明就里,却也生出几分不祥预感。
我抬手指向孙管家:"耀祖啊,让为娘给你引荐引荐。这位孙管家当年可是奉你父亲之命,将你抱回府中,亲手溺毙了我那苦命孩儿。"
复又指向中年妇人:"这位是梁产婆,二十年前正是她为柳清然接的生。你身上哪处有胎记,她可记得分毫不差。"
最后将目光落在书童身上:"至于这位,自幼跟在你父亲跟前当差。柳清然何时与你父亲私会,何时珠胎暗结,他比谁都清楚。"
"人证物证俱在,你们母子可还认账?"
裴耀祖脸色数变,仍强撑着冷笑:"便是证得我是柳氏所出又如何?纵使外室子,我体内终归流着父亲的血,这爵位合该由我承袭!"
柳清然惊惶不过瞬息,随即又挺直腰杆:"我儿说得极是!"
我轻笑出声,自袖中缓缓抽出一张泛黄契纸。
待看清我手中物什,柳清然顿时面如死灰。
"裴耀祖,你可知你生母柳清然乃官奴出身?"我将卖身契展开示众,"贱籍所生的孽种,也配肖想侯府爵位?"
"本夫人已从裴氏宗亲中择得良才,不日便过继名下。这世子之位,自当归他所有。"
柳清然嘶吼着扑将上来,却被翠云抬手拦住。
裴耀祖浑身剧震,踉跄后退:"不!这不可能!母亲三思啊!"
"爵位必是我的!只能是我的!"他突然调转话锋,双目赤红地瞪向柳清然,"都是你这贱婢挑拨!我娘分明是堂堂正正的侯夫人,怎会是你这低贱奴婢!"
说话间已抄起廊下木棍,雨点般的杖击径直落向瘫倒在地的柳清然。
"耀祖!我是你亲娘啊!"柳清然惨叫着抱头鼠窜。
裴耀祖却似疯魔般怒吼:"住口!你这下·贱胚子还敢胡言!"
他愈发癫狂地甩动着木棍。柳清然起初还能嘶声哭喊,渐渐地声息微弱,最终像破布娃娃般瘫在血潭里,显然已气绝身亡。
裴耀祖甩开染血的凶器,用袖口胡乱抹着掌心猩红,谄媚地凑到我跟前:"娘,儿子给您出气了!您瞧见没?那毒妇终于……"
两名侍卫横刀拦住他的去路。
"按大梁律例,弑母者当处凌迟。速去禀报府尹大人。"
我执绢帕掩住口鼻,血腥气熏得人胃里翻腾。
"娘!我是您亲骨肉啊!"裴耀祖发疯似的要扑过来,却被侍卫反剪双臂,"您仔细瞧瞧,我真是您怀胎十月生下的……"
我漠然颔首,侍卫立刻会意,将嚎哭的孽障拖出门外。那声嘶力竭的"母亲"在长廊里渐渐飘散。
转身推开紫檀屏风,塌上的裴延正剧烈颤抖。十年间反复昏迷早已将他折磨得不成人形,此刻枯槁的身躯陷在锦褥里,活似具披着人皮的骷髅。
今日未给他灌药,故而神志异常清明。这双浑浊老眼死死盯着窗外血泊,惊恐之色逐渐在褶皱密布的脸上蔓延。
"看见了么?"我指尖划过他凸起的喉结,"你们的好儿子,完美继承了柳氏的贪婪与你的狠毒。"
裴延喉咙里发出"嗬嗬"的破风箱声,枯枝般的手指突然揪住我裙摆:"妖……妖女……"
我弯腰逼近他青灰的面庞,发间金步摇在烛火下泛着冷光:"说对了,我就是来索命的恶鬼。当年你纵容柳氏毒杀发妻时,可曾想过有今日?"
他拼命往后缩,后背撞在拔步床雕花栏杆上发出闷响。门外忽然传来瓷器碎裂声——翠云正将滚烫的汤药灌进他嘴里。
我踱至回廊,晚风送来裴延含糊的呜咽。我听着悦耳,只感觉这个声音真好听!
(全文完)
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






